邊城翠翠(大地風華)
從邊城歸來,在很長的一段日子裡,我的眼前仍晃動著那根光澤锃亮的鋼纜。它穿過船體上的鐵環,橫跨江面固定在岸邊堅實的墩座上。我們上船后,一個苗族青年手持帶有凹槽的短木棒,在鋼纜上一卡一拉,船就順著鋼纜駛向對岸。
“由四川過湖南去,靠東有一條官路。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為‘茶峒’的小山城時,有一小溪,溪邊有座白色小塔,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。這人家隻有一個老人,一個女孩子,一隻黃狗。小溪流下去,繞山岨流,約三裡便匯入茶峒大河。”
由沈從文《邊城》開篇時提到這7個“一”,巧妙地鋪開,便牽出了一個動人的淒美愛情故事。從此,翠翠就活在許多讀者心中,沈從文的名字也和邊城緊緊地連在一起。2021年秋天,我第一次來邊城,是特意來尋訪邊城故事的誕生地。當時,我發現白塔下河邊上聳立著兩架水車。這是《邊城》中沒有提到的。可這兩架水車,卻勾起了我一番感慨。
水車極自然地成了見証邊城巨變的“時光老人”。我白天在邊城看到水,看到牌樓、石橋、村落、街道、小巷、碼頭和木船、竹筏、客棧、飯店門前懸挂的酒旗、燈籠,還有已被歲月風雨沖洗和人車踩出的深淺不一的印痕。這一切都在被旋轉歌唱的水車日夜不停地召喚著。
我在茶峒師范原址,看到依山而建、青瓦重疊有序覆蓋的音樂教室,似已有近百年歷史。每一片瓦都是一個歡樂的音符,似甘霖夜露、月色花香,在滋潤邊城一代又一代的心靈。想起沈老先生在書中所言:“一切河流皆得歸海,話起始說得極縱遠,到頭來總仍然是歸到使翠翠紅臉那件事情上去。”可令人感嘆惋惜的是在這個一腳踏三省的茶峒,翠翠與儺送等待的“明天”始終沒有到來。反而在一個風聲、雨聲、雷聲交加的夜晚,木船被波浪卷走,白塔被洪水沖塌,老船夫在風雨嘶鳴中死去,隻留下翠翠和一隻黃狗……
我第一次來到邊城,就把這些所看到、品味著的印象,形成了不同的畫面,留在心上。尤其是那水。水是多處流的,唯有這水對於邊城的人、邊城的生息、邊城的風致和愛情,就顯得尤為珍貴,甚至與命運相連。小說《邊城》也像茶峒大河的一束浪花,永遠流光溢彩地映照和滋潤邊城的歲月。亦如沈老先生所言:“我除了夸獎這條河水以外真似乎無話可說了。”我第二次來邊城,打算多住幾天,看看能不能在這裡遇見當今的翠翠。
我很幸運。曾經相識的湘西女作家龍寧英,她對當地文化很有研究。這次有她同行,自然就成了我的向導和老師。在採訪空隙,她不止一次用苗語給我們唱歌:
你歌沒有我歌多,我歌共有三雙牛耳朵。唱了三年六個月,剛剛唱完一隻牛耳朵。
是的,現在的邊城與3年前的邊城又不一樣了。在當下全域旅游掀起的熱潮中,邊城又煥發了青春的蓬勃,變得更加整潔、繁華、美麗。
在邊城,不知不覺就過去了兩天。
第三天,我決定去離邊城鎮幾公裡外的和平村,看看鄉村振興中的這座邊城新農村。清早,團團白霧還飄浮在蒼翠的山巒,田園村落都隱藏在茫茫白霧裡,眼前的一切如夢如幻。待太陽升高,白霧散盡,山野的一切都顯露出各自的姿態,放射著青綠黃紫的鮮活色彩。上午10點,穿過黑瓦白牆夾道的棟棟村民住宅,沿著彎曲村路,我們步行去看村上規模達4000畝的臍橙基地。望著山巒坡邊挂滿臍橙的果園,我轉身細細端詳眼前的80后女村支書曾華,覺得她正是我心中想象的當今翠翠。
此時,我想起了頭天下午與她在鎮上交談的情景。她穿一件白色短袖上衣,烏黑的短發,白淨的瓜子臉,一雙大眼睛。說話時,聲音悅耳,臉上不時浮起淺淺的笑窩。
我問曾華讀過《邊城》沒有?她說:“當然讀過,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書中的一段對話,其中有一句說‘別說一個光人,一個有用的人,兩隻手敵得五座碾坊!洛陽橋也是魯般兩隻手造的’。”我記起來了,這是書中老船夫與一個茶峒人的對話。后來,老船夫在心裡說:“翠翠有兩隻手,將來也去造洛陽橋吧,新鮮事!”
了解曾華的故事后,我才明白她為何喜歡這句話。她體悟到了其中的深意,我從內心佩服她。
曾華不是魯班,她不能造“洛陽橋”,可她用兩隻手和村民們造了一座“花果山”。在交談中,我還知道曾華的丈夫因一次車禍落下了終身殘疾,可他以驚人的毅力,克服身殘的困苦,仍去廣東打工,全力支持曾華的工作。而曾華珍惜丈夫的相助情誼,勇敢地挑起了養育兩個子女、操持家業、帶領全村脫貧致富、建設美麗鄉村的擔子。
望著眼前這個靈秀聰穎的女子,我真的無法想象她內心的明澈、她意志的堅強,她是怎樣堅持奮斗過來的。聽著她的含淚訴說,我被感動得淚花盈眶。我走進果園,用顫抖的手從樹上摘下一個帶著幾片綠葉的金色臍橙。我要帶回長沙去,與家人分享曾華和鄉親們一起創造的甜美生活。
我在邊城鎮採訪時,總會在不經意中,聽到鎮干部講起火焰土村的故事。我決定去實地察看。
火焰土村有202戶人家,長期以來散居在山巒坡邊。房屋底下都是已打通的礦洞。隨著時間的推移,如遇暴雨雷擊、山洪暴發,隨時都可能引來房屋的倒塌。站在我眼前的女村支書龍伍華,年齡並不大,可她飽經風霜的臉龐,極度勞累留下的走路姿態,使我對她的經歷產生了好奇。她對我說:“前些年,由於礦山的業主違規無序開採,整個山體百孔千瘡。好在近幾年從嚴督辦、整改,採取關礦、堵洞、墾復、栽樹還綠的舉措,才還了昔日的青山綠嶺。”
我爬上山梁,穿越荊棘叢生、已經封堵墾復的礦井舊址,就能看見腳下和遠處山巒已完全恢復良好生態。我心情慢慢舒展開來,不禁深深感嘆於沈從文那句“一切生命無不出自綠色,無不取給於綠色,最終亦無不被綠色所困惑。”這時,一個背著雙肩包的青年小伙子,趕著一群毛色油亮的黃牛,向山頭緩緩移動,一會兒就消失在一片綠色的叢林中。
返程途中,我想起沈老先生在《邊城》中的一段話:“詩人們會在一件小事上寫出整本整部的詩,雕刻家在一塊石頭上雕得出的骨血如生的人像,畫家一撇兒綠,一撇兒紅,一撇兒灰,畫得出一幅一幅帶有魔力的彩畫,誰不是為了惦著一個微笑的影子,或是一個皺眉的記號,方弄出那麼些古怪成績?”說得真好,真妙!我想沈老先生若地下有知,他看到今天的邊城鋪開的瑰麗畫卷,激蕩的歷史回響,呈現的美好生活風情,他或許會寫一個《邊城》的續集,描繪當代翠翠的傳奇。
《 人民日報 》( 2024年11月30日 08 版)
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
- 評論
- 關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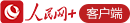




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
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
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
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
 關注人民網,傳播正能量
關注人民網,傳播正能量